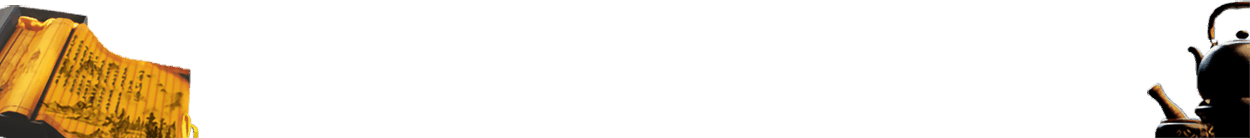|
日本禪茶流變史:幕府、茶道與禪宗的歷史互動
|
| 發佈日期::2020/1/22、瀏覽次數:258 |
|
在中國與日本的傳統文化中,禪與飲茶都是沉思與冥想的藝術,是思想與精神昇華的路徑。在日本禪茶的發展史中,茶道是如何與幕府貴族和禪宗發生關係的呢?日本禪茶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流變是如何互動的呢? 作者丨威廉·斯科特·威爾遜 沒有人能確言茶是何時傳入日本的。當然,公元前3世紀,經由朝鮮半島抵達日本列島的移民一定受過中國文化的燻陶。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文化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對日本產生了越來越深刻的影響。但並無史料可以說明,在日本的國家形態逐漸形成的過程中,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是否已經知道茶為何物或開始飲茶。可能他們知道茶這種植物,也知道如何飲用,只是不太重視。在一本中國早期的史書中,涉及日本的內容只記載了那裡的人生性快樂且好酒。 然而,到了公元6世紀,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並想方設法地學習,並將其引入自己的國家。儒家思想、佛教、詩歌、建築、城市規劃......日本從中國學到很多,其中就包括茶。茶常出現於中國詩歌,並為文人墨客創作詩文營造良好的氛圍。閒時飲茶能讓人走出日常生活,進入超凡脫俗的世界,讓人自覺與貴族、僧侶、文人同列。729年,聖武天皇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讀經會的第二天召百僧,賜之以茶。此時,茶不僅僅作為飲料存在,而且已形成一套十分接近宗教的文化。 真正將茶傳入日本的似乎是僧人空海。804年,他遠渡中國學習真言宗。空海天資聰穎,才華出眾,是一位宗教理論家、作家、書法家、藝術家、詩人、工程師......顯而易見,他十分擅長學習。他在長安學習佛法期間無疑有很多機會接觸茶,不管是在深夜苦讀時,抑或在莊嚴儀式上。僅兩年後,他便獲得正宗嫡傳名位,返回日本宣揚佛法。 806年,空海回日本時帶去了許多經書、注疏、佛像、曼陀羅和其他法器,當然也帶了茶葉,甚至可能是茶種。他向嵯峨天皇力薦茶,介紹其種種好處,天皇很快便喜愛上這種飲品。嵯峨天皇在一首致空海的詩中讚揚茶的魅力,並對空海即將返回山寺感到惋惜,他寫道:道俗相分經數年,今秋晤語亦良緣。香茶酌罷日雲暮,稽首傷離望雲煙。 本文出處:《禪與飲茶的藝術:安然度日的哲學》, [美]威廉·斯科特·威爾遜著,傅彥瑤譯,浦睿文化丨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 空海宣揚的佛法以及其中的美感對日本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影響了9世紀的茶湯以及茶道的產生。 真言宗認為,大日如來,也就是毘盧遮那並不脫離世間萬象,而普遍存在於世界萬物,且瞬息萬變。《大日經》是該部派最重要的經書之一,其中說道:“萬物本真。”而《大日經》的注疏提示我們:“佛不會出現在任何其他地方,只會在你眼前。”因此,雖然我們並無察覺,但大日如來不僅顯聖於現象世界中我們可感知的具體事物、情緒、思想中,而且通過它們向我們宣揚佛法和真理空海更進一步。他明白藝術既是“相”又是“相”的精煉表達,於是他說,每一次藝術創作都是佛祖顯聖的表現。換句話說,藝術與宗教本是一家。空海說,真如勝過相 (形式 ) 必須補充的是,對空海來說,藝術不限於繪畫,還包括雕刻、詩歌、散文、“行為舉止”以及文化、宗教活動中所用的器具。他的想法被日本人直觀地、積極地接納了,並在書法、能樂、茶道,甚至武士道等不同領域發揮作用。打坐與開悟以這些現實物件和形式化的動作為基礎,儘管這些物件和動作本身是世俗的,但它們不僅展現了佛陀,而且是恰當的思維方式的載體,是美好現實的體現。所以藝術即宗教,宗教即藝術,藝術形式中一個微妙的手勢便成為連接個人與宇宙的情態。 空海所處的平安時代的人們正在學習如何欣賞一碗茶的美,也在學習儀式與其涉及的對象。一碗茶,甚至可以具有超然的宗教意義。如此,空海最經典的“即身成佛”的境界便可通過既平常又藝術、既淨心又世俗的活動獲得。 大約在空海旅華400年後,另一位僧人榮西為了求法,展開了同樣艱險的旅途。榮西十分擔憂當時日本的佛教狀況:各部派間不斷發生武裝衝突,甚至同一部派內部也時有內訌。僧侶還尋求武士集團或貴族集團的支持,當時的京都即使稱不上混亂,至少也極不安定。榮西覺得佛教變得流於形式,僧侶忽視戒律,只執著於爭奪地位與權力。 1168年,榮西第一次來到中國。他潛心學習密宗教義,並於同年回到日本,希望用自己的新知識喚醒日本佛教。而到了1187年,隨著中央政府的瓦解,日本出現了更多的部派鬥爭,榮西明白自己的努力失敗了,必須再做一次長途旅行。他希望去中國和印度,雖然最後沒去成印度,但在中國停留至1191年。當再次回到日本時,榮西已擁有兩樣武器——禪與茶。這次,他覺得能夠拯救自己的國家了。 在中國,榮西發現禪宗是佛教裡唯一一種被重視的部派,而且禪宗似乎在宋代文化里發揮著極大的支撐作用。他熱心學習該部派的戒律和打坐法,閱讀《禪苑清規》。無論是在廟宇的儀式中還是私下的生活裡,榮西都飲茶,還鑽研茶的藥用功傚。 榮西回日本時取道鎌倉,將禪與茶介紹給當時的新政府。回到京都後,他將帶回的茶種分與少數僧侶。獲得茶種的僧人中有一位叫作明慧,在真言宗高山寺內種植了日本第一片茶園。 榮西堅信,嚴格遵守戒律與坐禪能夠振作日本國民的道德水平和精神狀態,而飲茶則能改善健康狀況。為此, 他寫了兩部論著,一部是《興禪護國論》,解釋了發展禪宗的好處,另一部是《吃茶養生記》 。《吃茶養生記》字數不多,通篇用漢語文言文寫成,非常切合實際地解釋了為何飲茶能促進健康。書中融合了儒家哲理和傳統中醫理論,又帶有真言宗的印跡,不過重點強調的是心是人體臟器的重中之重,而茶是心藥,為了健康,人人都應飲茶。 榮西的思想受到極大的重視,不過幾十年的時間,禪宗發展成日本國內的主要宗教和文化力量,而茶也變得無處不在。雖然他沒有寫過自己在中國參加的茶道儀式,也可能在回國後沒有跟其他僧人提起這些經歷,但後人一般認為,正是榮西使茶在日本普及開來的。在此值得附上《喫茶養生記》的一段內容: 茶也,養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山穀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 謂劫初人與天人同,今人漸下漸弱,四大、五藏如朽。然者針灸並傷,湯治亦不應乎…… 據說,榮西僅用一碗茶便治好了輔政者北條實時的重感冒。此事在幕府內傳開,茶也就此推廣開來,成為“國飲”。在其後的幾十年乃至幾百年間,各種飲茶方法逐漸形成。 禪與茶 榮西圓寂前一年,一位年輕的僧人拜訪了他。這位僧人也在尋找修佛的正確途徑,併且同樣對比叡山和其他僧眾集團感到失望。這位僧人就是道元 (1200—1253) 道元的著作和個人經歷中很少有跡象表明他有爽朗幽默的一面,他又常被描述為十分“獨立和固執”的人。因此,和道元一起飲茶或許是一件十分莊重的事;在其他寺廟亦然。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樣的茶事活動漸漸被社會大範圍地接受首先是武士階層,其後是商人,甚至還有農民。大眾爭相傚仿飲茶儀式中的禮儀做法,其中的莊嚴肅穆卻很快被忽略了。 禪宗與幕府在日本幾乎是同時出現的,武士們十分熱衷於修禪。雖然研讀經書也是修禪的一部分,但武士們並不將咬文嚼字視作通往開悟境界的途徑,反而十分依賴剎那的即時性和唯一性,相信打坐時萌發的直覺。禪宗認為,開悟關乎生死,而“生死”這個詞與概念是武士十分明了的。與禪一同興起的還有茶以及莊嚴又引人入勝的飲茶儀式。 然而武士終究不是僧人。百年之內,這個新崛起的階層就在品茶活動中加入了賭博和競賽,並將窮奢極欲的作風帶進他們進行茶事活動的場所,將飲茶變成娛樂,而非肅穆的儀式。有記載稱武士的茶室內有豹皮鋪於椅凳,滿室中國和日本的珍品,品茶大賽的勝出者會得到十分昂貴的獎品。加之從13世紀起日本全境開始茶葉種植,茶及其社會屬性變得唾手可得。從武士到農民,人人都有機會接觸茶,只有一小部分極其貧苦的人被稱為“水吞百姓”,意為“喝水的人” 。 最終,娛樂性的飲茶不僅在武士階層,而且在佛教僧侶、神道教的神職人員、貴族和新興的富裕商人間都流行起來。至15世紀,斗茶和茶會發展得過於繁盛,以致官方不得不下令禁止,然而傚果併不顯著 茶道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有趣的是,日本飲茶文化向現代茶道的轉變正發生於武士階層內部自上而下地實現。將軍與其最貴族化的家臣併不是沒有審美能力,而且他們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需要會鑒別、護理和展示中國藝術品的助手,這樣才能用自己的藏品讓同僚大開眼界。這些精於藝術又有品位的助手在日語里叫作“同朋 眾”。他們不一定是僧侶,但都剃了頭,取名都以“阿彌” 結尾,以此暗示與阿彌陀佛的聯系。 能阿彌 (1397—1471) 村田珠光,出生於古都奈良,他給自己搭了一間小茅屋用於坐禪、飲茶,由此為茶道建立了一套新標準。珠光曾經很苦惱因為他對待師父態度懶散,坐禪時常常打瞌睡。他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一位大夫,大夫顯然對榮西的《喫茶養生記》十分熟悉,為他開了一味藥茶。中國詩歌中多有結廬山野的描寫,珠光或許是受此影響。也許,影響他的正是陶淵明的《飲酒 (其五) 珠光割了芒草,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屋 (珠光的父親既是僧人也是木工好手) 從珠光起,禪與茶便由壁龕內的字軸引導展開。茅屋雖小,珠光卻不介意。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那個故事,佛陀弟子捨利弗被問道:“維摩詰小小一室,眾菩薩、聞聲如何能坐?”而他回答:“我們來此是為聽法,而非一席之地。”珠光也在簡單、樸實的茅草屋裡找到了修禪、習茶之所是其他人進一步發揚了“禪茶一味”這一觀念的美學價值,大書特書禪與茶之非同尋常的也另有其人;但不要忘記,是珠光帶領我們進入了這茅屋中的寧靜與平和,讓我們坐在字軸旁,與祖師為伴。在茶道中,這種狀態一直延續至今。 祖師 珠光於15世紀末在日本建立起的這一套飲茶禮儀,中國早在四五百年前就有了。中國禪僧在寺院裡自己的房間中或別處掛上師父或師爺的書法作品。這些作品通常是師父的箴言抑或引自禪宗經典,成為冥想的出發點,為在坐禪或在寺院做雜務的僧人指明方向,珠光從一休那兒獲得的那幅字出自中國禪師圓悟克勤之手,上有數行漢字,因而較寬。這樣的字軸上通常寫著禪語或中國古文經典的選句,在17世紀前十分流行。而17世紀時出現了只有一行字的字軸,內容引自禪宗經典,這一形態被認為更直接和恰當。 這些一行物更好讀也更易懂,其內容很快便從禪宗拓展到人們熟悉的儒家、道家經典,還有中國古詩。正如前面提到的,從單個漢字到整首詩,現在“一行物”一詞可以指代任何字軸。它們出現在茶室、餐廳、住宅、道場裡,甚至出現在新年時市場販賣的日曆上。實際上,在日本這個文學素養極高的社會裡,一行物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於是,現在我們能坐下來,和釋迦牟尼、老子、莊子、孔子、孟子、陶淵明、臨濟義玄、雲門文偃、無門慧開、 白居易、蘇東坡、寒山、趙州從諗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一起品茶。而達摩、空海、宗賾、榮西、道元、能阿彌、村田珠光這些人為我們構建了這場儀式的基礎,使得我們在茶室內與他們共享同一空間。坐在我們身邊最尊貴的客人,很有可能就是神農。 最後,茶之集大成者千利休邀我們讚美“賞筆者之德”,並領會藏於墨跡間的真正意味。 書法與禪的聯繫最早出現在中國宋代,大約成熟於黃庭堅的時代。黃庭堅雖然是保守的儒士,卻熱心地拜師修禪,並驚訝地發現在頓悟後,自己的書法發生了轉變。他揮筆自由如有神,可以完全地表達內心世界。和珠光一樣,黃庭堅十分崇拜陶淵明,並將陶詩喻為“無弦琴上單於調”, 而他自己的作品也出現瞭如此禪意。 通過黃庭堅和其後幾位中國禪師的書法,人們很快便明白了這種藝術本身也可作為修禪的途徑。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人,包括榮西和道元,不僅為自己的寺院帶回書法作品,而且開始實踐這種藝術,並最終形成了日本書道。 禪或茶,都要求我們完全投身於當下的瞬間。道元在他的《知事清規》中提醒我們,當我們在洗衣做飯時不該被其他思緒打擾,不該思慮接下來要做什麼,不該擔心股票和債券,甚至不該期望得道。我們應該專注於眼前所做之事,就像武士道要求習武之人手腳身心與劍合一:流露無礙。 正如書法,如果筆、墨、紙於手中統一,書寫者不再介意規則和技巧,那麼筆的律動便是心的律動。那一筆一畫見證的不是書寫者的技藝,而是其內涵和對所寫理解的深度。書寫者所選的這一句是否反映了他的領悟?行筆是否表明其心境?在中國和日本有一句老話說的就是這件事:心正即筆正。 或許我們會問自己,我們又有什麼領悟或正見的能力呢? 珠光會告訴你,就在你眼前,且看,且喫茶。 本文選自威廉·斯科特·威爾遜所著的《禪與飲茶的藝術:安然度日的哲學》引言部分,由浦睿文化授權刊發。 作者丨威廉·斯科特·威爾遜 摘編丨吳鑫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翟永軍 |